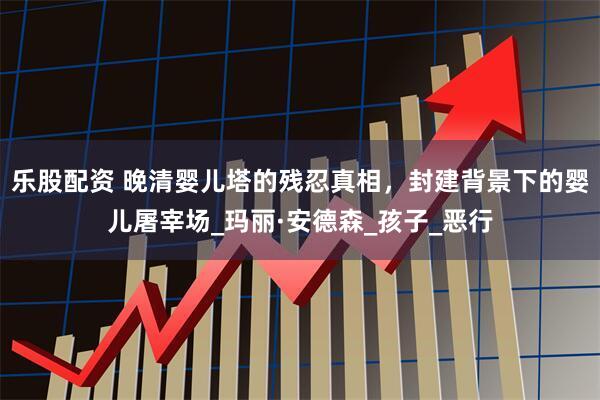
在您阅读本文之前,请您先点击“关注”,这样便于您参与讨论和分享,您也会体验到一种独特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与关注。
文 | 方丈
编辑 | 幸运
初审 | 天坛
表面上看,这似乎只是一座普普通通的塔,然而它既没有佛像的虔诚,也没有钟声的悠扬,弥漫在周围的只是无尽的沉默和阴冷。在清末某些地方,确实存在着这样被称为“婴儿塔”的建筑,然而它并非令人惊叹的奇观,而是一个又一个吞噬生命的无声墓地。
那些刚出生的婴儿,因性别、贫穷或迷信等各种原因被冷酷无情地抛弃。塔下不仅堆积着纤细的尸骨,更是一代代人对生活的无奈与残酷的反映。难以理解的是,一个无辜的婴儿,竟连啼哭的权利都被剥夺了?
展开剩余84%19世纪末的某个清晨,雾气尚未散去。一位金发碧眼的英国女画家玛丽·安德森,怀抱着画具和相机,在福州城外进行写生。她是一位热爱东方文化的艺术家。
“那边的小塔真有趣。”玛丽指着远处一座泛着古怪气息的建筑对向导说道。向导的脸色瞬间变了,“洋小姐,那地方不吉利,我们去别的地方吧。”
然而,玛丽的好奇心被激发了。她坚定地要求去探个究竟,向导无奈,只能硬着头皮带路。逐渐靠近,一个刺鼻的腐臭气味扑鼻而来。玛丽掩住鼻子,仔细打量这座“塔”。它约有一米高,用青砖和石头建成,形状方方正正,底部封闭,顶部则开了一个方形洞口。
“这是什么用途?”玛丽问。向导犹豫了半天,最终叹了口气:“洋小姐,实话跟您说吧,这是婴儿塔,专门……专门放死孩子的。”
玛丽的心顿时沉了下来,她的手在抖动,举起相机时快门声响起,那一刻她不知道自己所记录的是怎样一段人间炼狱。若不是她的镜头,或许这一段历史将被彻底封存。旁观者的视角有时反而能看到当事人早已习以为常却极为残酷的真相。
婴儿塔的初始设立,实际上是出于几分悲悯。晚清时期,医疗条件极其落后,婴儿夭折的比例令人震惊。十个婴儿里能存活六七个,算是幸运。穷人家的孩子若生病,往往因为无钱请医,只能眼睁睁看着他们离世。“孩子走了,总得有个去处吧。”曾有位老妇人如此感叹,“买不起棺材,也没地方埋,总不能把他们丢在路边让野狗叼走。”
因此,一些心怀善念的人出资建立了婴儿塔,专门安放夭折婴儿的遗体。每隔几天统一火化,多少算是给这些小生命一个体面的归属,收费也不高,50文钱相当于两斤米。然而,人心的善良经不起考验。
渐渐地,借机谋利的人开始出现了。“反正都是要烧的,活的死的又有什么区别?”这种扭曲的想法如瘟疫般蔓延。经过大量史料的查阅,我发现婴儿塔从“善举”转变为“恶行”不过数年。人性一旦释放出恶,就如同打开潘多拉的盒子,原本充满慈悲之心的管理者,逐渐变成了麻木的刽子手,听到塔中哭声时,也只有当作风声而已。
而在这种惨淡的现实中,婴儿塔里最多的是哪种孩子?让人心寒的是——95%以上都是女婴。“生了个丫头片子,真是晦气!”这是当时许多家庭的第一反应。在那个男尊女卑的年代,女性被视作传宗接代的工具,不得受教育,不得抛头露面,长大后更是被嫁出,宛如泼出去的水。相反,男孩则被视为家中的香火,延续家族的希望。
我曾在一份晚清记载中看到如此故事:福州有位姓陈的商人,家庭境况还算不错。他妻子接连生下四个女儿,让他十分恼怒。第五胎仍然是个女孩,接生婆刚说出“是个千金”,他便阴沉着脸离开了。当夜,陈商人命下人将新生女婴放入篮子,趁着夜色送至城外的婴儿塔。那孩子撕心裂肺地哭着,而陈老板只是冷冷地说:“养不起就别养,省得将来成了赔钱货。”
更令人愤怒的是,这样的事情当时屡见不鲜,邻里们不仅不觉得残忍,反而认为陈商人有“魄力”。我认为,这种对生命的漠视根源于整个社会扭曲的价值观。当社会将人分成三六九等,以性别作为评价标准时,悲剧自然会接踵而至。被抛弃的女婴们,她们的“罪过”只是生错了性别。
生活在婴儿塔附近的人,常常在深夜能听到怪异的声音。“像猫叫,又像是风声。”一位老农这样形容。然而,大家心里都明白,那并非猫叫,更不是风,而是被抛入塔中、尚未断气的孩子在哭泣。
有一位姓李的先生,曾在日记里记录过这样一件事情:“癸巳年七月十五,中元节。夜半被哭声惊醒,声音从西边的婴儿塔传来。起初以为是鬼魂作祟,后知是活婴在哭。心中不忍,却又无能为力,辗转反侧,一夜未眠。”李先生第二天去找婴儿塔的管理者,想要救出孩子,却只换来冷笑:“李先生,要是您有闲心,不如多教几个学生,您管不了的。”
最可怕的并非恶行本身,而是社会对恶行的麻木。当整个社会都认为这事“正常”时,个人的良知显得多么无力。我在想,如果当时有更多像李先生这样的人站出来,或许历史会有所不同。然而,沉默的多数选择了视而不见,而这种集体的沉默恰恰是对罪恶的纵容。
您以为婴儿塔仅是历史的遗迹?大错特错,它的阴影仍延续至今。2014年,广州设立了“婴儿安全岛”,本意是给那些被遗弃孩子提供生存的机会,但短短一个多月,便收容了200多个弃婴。讽刺的是,许多送孩子来的并非穷人,而是开着豪车的“体面人”,他们将孩子放下转身便走,毫不回头,工作人员打开襁褓后发现,大部分都是健康的女婴。
“现在是什么年代,怎么还有这样的事?”一位工作人员忍不住泪水。确实,已经是21世纪了,我们拥有高铁与智能手机,但有些人的思想却仍停留在百年前。我觉得最悲哀的是,这些父母或许还认为自己是“文明的”——至少他们没有将孩子丢进婴儿塔,而是送到了安全岛。然而本质上又有什么区别呢?都是因为孩子的性别不符合他们的期待,便剥夺了孩子被爱的权利。
有人说,生孩子不需要考试是这个世界最大的缺憾。我对此深有同感。那些把孩子视作私有财产并随意处置的父母,是否配得上“父母”这一称谓?婴儿塔早在历史的尘埃中坍塌,但它留下的伤痕依旧。每一个被遗弃的孩子背后,都折射出成年人自私与冷漠的底色。历史不应被遗忘,因为忘记过去便意味着背叛。那些曾经在黑暗中哀哭的小生命,值得被铭记,也促使我们反思:文明,究竟意味着什么?
——信息来源:
- 英国女画家玛丽·安德森福州摄影集(1890年代)
- 《晚清笔记汇编》
- 《福州地方志》
发布于:山东省汇盈策略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